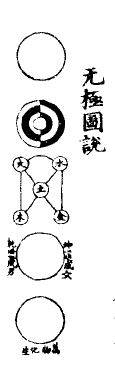陈撄宁
神经衰弱症,目前尚无良药可医,含磷质的药品虽号称补脑,亦嫌名实不符;其它一切兴奋剂,或镇静剂,只能收暂时的效用,药性过了,仍旧是衰弱,或更加严重。使脑神经绝对安静,排除一切思想,这是下手工夫最要紧的原则,也是神经衰弱最有效的良方,但因人们思想习惯,由来已久,要它一旦停止不动,很难办到;为达到这个目的,古人就立出许多法门,比较起来,以庄子“听息”法为最好。
所谓“听息”法,就是听自己呼吸之气,初下手只用耳根,不用意识,并非以这个念头代替那个念头,更不是专心死守鼻窍或肺窍,也不是听鼻中有什么声音,只要自己觉得一呼一吸的下落,勿让它瞒过,这就算是对了;至于呼吸的快慢、粗细、浅深,皆任其自然变化,不用意思去支配它,听到后来神气合一,杂念全无,连呼吸也忘记了,渐渐地入了睡乡,就要乘这个机会熟睡一番,切不可勉强提起精神和睡意相抵抗;睡醒之后,可以从头再做听呼吸法,又能够安然入睡。若是在白昼间睡了几次不欲再睡时,不妨起来到外面稍为活动,或拣树木多、空气清洁的地方,站在那里做几分钟吐纳工夫也好,或做柔软体操、练太极拳也好,但要适可而止,勿使身体感觉疲劳;回到房内,或坐或卧,仍旧做听呼吸的工夫,还可能入于熟睡的境界。
凡患神经衰弱的人,大半兼有失眠症,安眠药片不宜常服,只有听呼吸一法,可以根本解决问题,毫无流弊,而且与《黄帝内经》上所说阳入于阴的理论相合(《灵枢·大惑论》:“卫气常留于阳,则阳气盛;不得入于阴,则阴气虚,故目不瞑。”)
前人书中常有“心息相依”这一个专门术语,但未说明如何依法。苏东坡的工夫,是先用数息法,后用随息法;朱子《调息箴》的工夫,则用《楞严经》“观鼻端白”法。但数息要用意去数,不能纯然无念;观鼻要开眼去观,时候久了,眼神经难免疲劳;只有《庄子》听呼吸法,心中不需要起念,久听也不觉疲劳,才真能合于“心息相依”这个轨辙。今将这三种方法列举如下,并加以浅释,好让学者自己去实验。
一、苏东坡养生说(见东坡《志林》卷一):
原文:“已饥方食,未饱先止;散步道遥,务令腹空;当腹空时,即便入室;不拘昼夜,坐卧自便;惟在摄身,使如木偶。……又用佛语,及老聃语,视鼻端白,数出入息,绵绵若存,用之不勤。数至数百,此心寂然,此身兀然(兀音屋),与虚空等,不烦禁制,白然不动;数至数千,或不能效,则有一法,其名曰随,与息俱出,复与俱入;或觉此息,从毛窍中,八万四千,云蒸雾散。无始以来,诸病自除,诸障渐灭,自然明悟:譬如盲人,忽然有眼,此时何用求人指路,是故老人言尽于此。”
浅释:注意养生的人,食物要有节制,必须等到腹中觉得饥饿时,才可以进食,尚未吃得十分饱满,就应当停止;每餐后宜到室外空旷地方自由自在的散步,使腹中的食物大部分都消化了,此时就回到房里去准备做静功;不论是白天或是夜晚,也不论用坐式或用卧式,听各人自便;只要管住自己身体不让它动摇,像木头人一样,就算合法。身体已经安置好了,即照佛家所说的法门和老子所讲的工夫合起来做,用两眼观看自己的鼻尖,并同时用意数鼻中呼吸出入的次数,要诀贵在勿忘与勿助,勿忘就是绵绵若存,勿助就是用之不勤。普通数息法,若数出息即不数入息,若数入息即不数出息,一呼一吸,只算一次,不能算两次。数到几百次以后,心中寂然如虚空,身体兀然如山石,不需要勉强去禁止或制伏它,身心二者自然都安静而不动了。数到几千次以后,或无力再数下去,此时另有一个法子应付,叫作“随”字诀,当息出时,心也随它同出,当息入时,心也随它同入;有时或感觉这个息似云雾蒸发散布于周身无数的毛孔中(原文“八万四千”是形容身上毛窍之多,不是实在的数字),不由鼻孔出入。工夫做到这样地步,久远以来的各种病苫和障碍,都能够逐渐灭除,心里也就自然明白而开悟了;譬如瞎子,此时忽然眼睛透亮,自己能够看见道路,用不着再要求他人指引了。
二、朱子调息箴(《朱子全集》第八十五卷):
原文:“鼻端有白,我其观之;随时随处,容与猗移(容与,闲暇舒适之义。猗音依,猗移,随顺之义)。静极而嘘,如春沼鱼;动极而翕(翕音习),如百虫蛰。氤氲阖辟,其妙无穷。谁其尸之(“尸”字作“主”字解),不宰之功。”(后四句节略)
浅释:观鼻端白,原是佛教《楞严经》上二十五个圆通法门中第十四个法门,苏东坡、朱晦庵两人都采用了这句话,但他们的说法并不完全和《楞严经》相同。朱子的意思是说:做这个工夫,不论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,身体总要安闲而舒畅,不要弄得周身难过;又要心平气和、顺其自然,不要勉强执着。气机静到极处,它自然要动,就像春天的鱼类,浮在水面嘘气;气机动到极处,它自然要静,就像冬天的虫类,伏在土里翕气(“翕”是聚敛收摄之义)。此时身中之气,交互团结,有天地氤氲之象;一动一静,有乾坤阖辟之机,妙处是说不尽的。若问是谁在那里做主?其实并无所谓主宰,而是自然的功能。
三、庄子心斋法(《庄子·人间世》):
原文:“颜回曰:敢问心斋?仲尼曰:若一志;无听之以耳,而听之以心;无听之以心,而听之以气;听止于耳,心止于符。气也者,虚而待物者也,唯道集虚,虚者心斋也。”
浅释:颜回是孔夫子的学生,仲尼是孔夫子的外号。颜回问“心斋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?孔夫子说,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,不要胡思乱想;等到念头归一之后,就用“听”字诀,但不是用耳听,是用心听;这还是粗浅的说法,就深一层工夫讲,也不是用心听,而是用气听;到了这样境界,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了,神和气两者合而为一,心也不起作用了。气的本质是虚的,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,只有“道”这个东西常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,工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虚一样,就算是心斋。以上是孔夫子告颜回所问心斋工夫的做法。这种工夫是一连串做下去的,中间本无所谓阶段,但为学者容易入门起见,不妨在整个工夫中划分几个步骤,再详细的加以说明:
第一步,“若一志”,“若”字作“你”字解。“志”就是思想,也可以说是念头。当起首做工夫的时候,心中思想要专一,不要有许多杂念在里面打搅,杂念如果不扫除干净,工夫很难做得好。
第二步,“无听之以耳,而听之以心”,“无”等于“毋”,也可以作“勿”字解;“之”字是代名词,指所听的对象而言;“以”字作“用”字解。念头归一了,就井始做工夫,用“听”字诀。普通所谓听,本是用两个耳朵听各种声音;此处所谓听,决不是听声音。人们就要发生疑问了:既说是听,必有所听的对象,不听声音,又听什么?这个问题,在各家注解上都找不到明确的回答。今日特为指出,初下手就是听鼻中呼吸之气。凡呼吸系统正常而不发生障碍的人,鼻中气息都没有声音,所以说“勿用耳听”;虽是没有声音,但自己却能够知道鼻中气息一出一入,或快或慢,或粗或细,纵然是聋子,也会有这个感觉,所以说“听之以心”。
第三步,“无听之以心,而听之以气”,此处又引起问题了;心是有知觉的,还可以说得上一个“听”字;气是没有知觉的,如何也能够用它来听?心所听的对象是气,气所听的对象又是什么?若说用气来听气,这句话在埋论上讲不通,究竟怎样解释才好?答曰:听息的工夫做得时间长久,心和气已经打成一片,分不开了,气不能作为心的对象了,不能再说用这个心听那个气,所以说“无听之以心”。此时身中的神和气虽然团结在一起,尚未达到混沌境界,还稍为有点知觉,继续做下去,并不需要很多时间,自然就完全无知觉了。从有知觉到无知觉这一段暂时的过程中,与其说以心听气,使心和气相对立,不如说以气听气,使心和气二者之间泯去裂痕,所以说“听之以气”。此处虽仍旧“听”,实际上就是不要再着意于“听”,成语所谓“听其自然”、“听之而已”、“听他去罢”,这几个“听”字是此处最好的解释。
第四步,“听止于耳,心止于符”,初下手做工夫,注重在“一”字诀;等到念头归一之后,就注重“听”字诀;假使长久的抱住一个“听”字不肯放松,也嫌过于执着,再后就要用“止”字诀了,所谓“听止于耳”,就是教人不要再着意于听。此时,工夫已渐渐的入于混沌境界,身中的神气合一,心的知觉已不起作用,所以说“心止于符”(符即是与气符合之义)。这种神气合一的状态是无知无觉的,外表上看来和睡着了一样,但内部的情况是不相同的。
第五步,“气也者,虚而待物者也,唯道集虚,虚者心斋也”。以前由浅而深的境界,一步一步的都经过了,最后到了“虚”的境界。这个“虚”是从无知无觉以后自然得到的,不是用意识制造出来的,如果做工夫时候,心里常常想着要虚,反而不能虚了。全部工夫原是由后天返还到先天,所以第五步工夫,应该就先天境界去体会。若问如何叫作先天,这件事已越出疗养法范围之外,此处不必深谈。普通用静功疗病;只要做到身中神气合一的境界(即心止于符)已足够了。
今将以上所列三种法门作一个总结:苏东坡是先数息,后不数;他所谓“随息出入”,就是随其自然,不要再去数它。朱晦庵是先观息,后不观;他所谓“不宰之功”,就是顺其自然,不要再去观它。庄子是先听息,后不听;他所谓“听止于耳”,就是任其自然,不要再去听它。三人下手的工夫虽然不同,后来都归到一条路上,学者可以参合而用之。青年神经衰弱者,用此法三个月,可以愈十分之七八;中年神经衰弱者,用此法三个月,可以愈十分之五六。但病有轻重之别,此指病重者而言,病轻者差不多可以全愈。出疗养院后,回到工作岗位时,每日早晚仍宜抽空做两次,勿使间断,才能继续维持已得之效果,逐渐完成未了之余功。
附:治遗精的特效内功
遗精这件事有生理关系和病理关系之不同,年轻人半月一次,中年人一月一次,这是生理上常有的现象,不能说它是病。若一星期有数次之多或性交无力、滑流不禁者才算是病态,急须要治好,否则身体永无健康之望。因为神经衰弱,性器官无控制力,所以常患遗精病。因为泄漏太多,神经缺乏补养之源,遂致更加衰弱,此两者互为因果,遗精病若不治好,神经衰弱恐难收全功,所以又附录此一法,使动功和静功相辅而行,是法始称完备。
静功疗治神经衰弱,虽大有效果,但对于防止遗精尚无显著的功效。气功有时虽能治遗精,有时亦不起作用,假使做得不好,遗精反而加甚。唯有此处所说的运动法个个有效,此法要在床上做,床要一头高一头低,高低相差六、七寸,下面是硬板,上面铺厚褥。若是钢丝床、棕榻床皆嫌太软,不合用。静功也需要这样的床,前面问答中已提及。
这个动功是专门锻炼腰肾和精窍部份,每天要做二次。一次在晚间就寝拟用睡功,尚未卧下时;一次在早晨睡足将要起身,尚未下床时;先坐在床上,面向床低处,背向床高处,两腿向前平伸勿曲,脚尖朝天,自腰以上,身体挺直,两手掌搭于两膝盖骨,是为预备姿式,然后分成三个动作:
(一)两手握拳,将两拳缩回,紧贴于左右肋下,肘尖尽量伸向后方。
(二)再将两拳分开,掌心朝天,由两耳旁向上直托,似举重物,两臂伸直勿屈,使两手臂覆向头顶,两眼仰视两手臂。
(三)再低头弯腰,同时将两臂向上伸直的姿式改为向下向前直伸,使手指碰到脚趾尖,再回复到身体正坐,两手搭膝的原状。
此(是)为一遍运动完毕,第二遍仍如原法。初做以十遍为度,可以多练几天,等到做熟以后,即逐日增加一遍。做到二个月以后,可以每次做六十遍,连最初的十遍计算,计七十遍。如果身体衰弱,气力不足做七十遍,也可以减少次数,或五六十、三四十也无妨,但至少每次要做三十遍。若问每遍动作快慢如何?最好宜慢不宜快,一分钟最多只许做五遍,六分钟做三十遍。
做这个功有一件事须要注意:当低头弯腰,手指与脚尖接触时,两腿要伸直,不可弯曲。普通未曾练习之人,此时若将两腿伸直,每苦于手指和脚尖距离数寸之远,很难碰到一处,但也无妨。只要每日照样做,总有一日能够碰到。
正当低头弯腰手指攀脚尖时,两腿如果十分伸直,丝毫不屈,后腰部和两腿弯必定发酸,肾囊后和肛门前必定拉紧,会阴部必定和床褥互相摩擦;这些就是治遗精病特效的作用。要稍为忍耐一点,不可畏难终止,但也要依次前进,不可蛮干!每次无论多少遍,做完之后需要休息,即在床上静坐三十分钟,勿急于下床。
此法不但能治夜梦遗精,纵然比遗精更严重的白昼滑精或性交早泄也能治愈。若已婚的男子,不住医院而住家中,正当练功的时期,务必分床独宿,禁止房事三月(时间能长则更好),否则今日尚未将关窍收紧,明日又去把它打开,那是永远练不好的。
另有呼吸升降作用、意识导引作用都是身体内部的事。若能同时和外部的运动并做,效力会更大更快,在短期间就可以紧闭遗泄之门。但因做法复杂,今为避免困难起见,所以此处不谈,普通患遗精病者,仅做外部简单运动已够用了。
如果每天不断的做,二、三个月之后,必有良好的成绩表现出来,足以使练功者增加自信心。
读静功疗养法书后
一、本书说原理处,真如白香山诗,老妪都解,绝不引用玄学名词,使人坠入五里雾中,东西莫辨。
二、本书说方法处,剥茧抽丝,深入浅出,极精微而道中庸,若非胸怀淹博,更辅以深厚之阅历经验,何能道其只字。
三、从前师弟授受修养功法,不免带有玄奥性质,而于著书立说,尤多隐约其辞。以口头语,以真实语而述,切合实用之详细修习步骤及过程如此书者,尚未之见。抑亦所谓天不爱道,时代使然?
四、本书末附(治)遗精特效法,系作者采用菲岛弟子洪太庵所倡弯腰攀足、长筋之术,经作者修正,增列缩肘与托天等配合动作后,太庵呼谓有点铁成金之妙。此法曾经在孙镜阳先生处之同道、中和子曹昌祺君,行之而立奏功效。
五、庄子心斋之法,前经作者语诸:安徽怀宁胡渊如老先生,胡君惊为空前之发明。乃于师范学校讲述庄子之余,转授李朝瑞君。李君行之,不期年,竟完成化气之功,而达可进修化神初步阶段。此虽由于李君年事尚轻,有此佳境,惜后未见其进而从事专修耳。
六、人类生命,所赖以维持者,全仗一点带来之生命潜能,此种本元潜能,即同属于宇宙之大能。生命潜能,如已耗竭,虽有特效药物,亦无法回天。药物不过袪除障碍,助长本元潜能、发挥其原有之功力而已。如欲固本培元,必须绝缘根尘之接触,停止心识之现行为其梯基。此中精理,已为中华数千年前所明察,而用以修养,不亦奇且伟欤!
七、此书虽专指治疗神精衰弱,然就所举疗愈胃溃疡经验,不止一次而言,可知本书绝非单治神经衰弱一症,勿被瞒过者一。本书虽标题作治疗之用,而实际上乃一普遍适用之修养专籍,亦且为习气功者所必需,勿被瞒过者二。本书绝未提及道门玄功字样,而实则无异为一道门要典,玄功初基之宝筏,勿被瞒过者三。
八、作者过去,时常不断有同好者,请其推介,有无典籍切实适用、而无流弊,可以阅读而依之起修者,惟搜遍古今,都难惬意。兹篇之作,则此种困惑,嗣后当可不复存在。而加惠后来,功且无际。
九、本书后段,附有苏子随息,及朱子调息两篇,然仍应以庄子心斋一篇为修习主要对象。虽本书为初阶之作,于先天一着,无事赘言,但已足够应用。如能玩索有得,熟习于心,一旦虚室生白,吉羊止止,诚如苏子之言:“诸障渐灭,自然明悟”。则一言半句,便可通玄,自有黄鹂报好音也。